亲爱的朋友:
您的信让我激动,因为借助这封信,我又看到了自己十四五岁时的身影,那是在奥德亚将军独裁统治下的灰色的利马,我时而因为怀抱着总有一天要当上作家的梦想而兴奋,时而因为不知道如何迈步、如何开始把我感到的抱负付诸实施而苦闷;我感到我的抱负仿佛一道紧急命令:写出让读者眼花缭乱的故事来,如同那几位让我感到眼花缭乱的作家的作品一样,那几位我刚刚供奉在自己设置的私人神龛里的作家:福克纳、海明威、马尔罗、多斯·帕索斯、加缪、萨特。
我脑海里曾经多次闪过给他们中间某一位写信的念头(那时他们还都健在),想请他们指点我如何当上作家。可是我从来没有敢动笔,可能处于胆怯,或者可能出于压抑的悲观情绪——既然我知道他们谁也不肯屈尊回信,那为什么还要去信呢?类似我这样的情绪常常会白白浪费许多青年的抱负,因为他们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文学算不上什么大事,文学在社会生活的边缘处苟延残喘,仿佛地下活动似的。
既然给我写了信,那您就没有体验过这样的压抑情绪,这对于您愿意踏上的冒险之路以及您为此而期盼的许多奇迹,是个良好的开端——尽管您在信中没有提及,但我可以肯定您是寄希望于奇迹的。请允许我斗胆提醒您:对此,不要有过高期望,也不要对成就抱有过多幻想。当然,没有任何理由说您不会取得成就。但是,假若您坚持不懈地写作和发表作品,您将很快发现,作家能获奖、得到公众认可、作品畅销、拥有极高知名度,都有极其独特的走向,因为有事这些名和利会顽固地躲避在那些最应该受之无愧的人,而偏偏纠缠和降临到受之有愧的人身上。这样一来,只要把名利看作对自己抱负的根本性激励,那就有可能看到梦想的破灭,因为他可能混淆了文学抱负和极少数作家获得的华而不实的荣誉与利益。献身文学的抱负和求取名利是不相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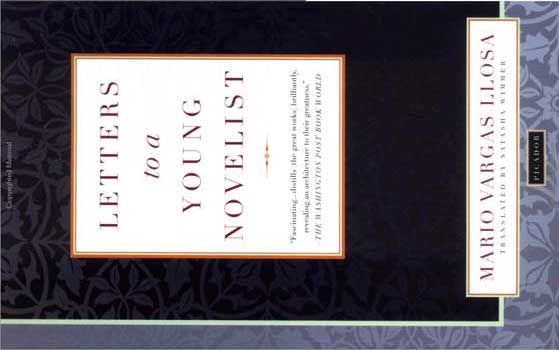
文学抱负的基本属性是,有抱负的人如果能够实现自己的抱负,那就是对这一抱负的最高奖励,这样的奖励要超过、远远地超过它作为创作成果所获得的一切名利。关于文学抱负,我有许多不敢肯定的看法,但我敢肯定的观点之一是:作家从内心深处感到写作是他经历和可能经历的最美好事情,因为对作家来说,写作意味着最好的生活方式,作家并不十分在意其作品可能产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后果。
谈及怎样成为作家这个振奋又苦恼的话题,我觉得文学抱负是必要的起点。当然,这是个神秘的题目,它被裹在不确定性和主观性之中。但是,这并不构成用一种理性的方式加以说明的障碍。只要避免虚荣心,只要不带迷信和狂妄的深化色彩就可以进行。浪漫派一度怀抱这样的神话:把作家变成众神的选民,即被一种超自然的先验力量指定的人,以便写出神的话语,而只有借助神气,人类将神才可能得到升华,再经过大写的”美“的感染,人类才有可能得到永生。
今天,再也不会有人这样谈论文学或者艺术抱负了。但是,尽管现在的说法不那么神圣或者辉煌,抱负依然是个相当难以确定的话题,依然是个起因不详的因素;抱负推动一些男女把毕生的精力投入一种活动:一天,突然感到自己被召唤,身不由己地去从事这种活动——比如写故事,根据自身条件,使出浑身解数,终于觉得实现了自我的价值,而丝毫不认为是在浪费生命。
我不相信早在妊娠期上帝就为人的诞生预定了一种命运,我不相信什么偶然性或者乖戾的神意给在母腹中的胎儿身上分配了抱负或者无能、欲望或者无欲。但是,今天我也不相信青年时有一个阶段在法国存在主义唯意志论的影响下——尤其是萨特的影响——曾经相信的东西:抱负是一种选择,是用什么来决定人未来的个人意志的自由运动。虽然我认为文学抱负不是镌刻在未来作家身上基因的预示性东西,虽然我坚信教育和持之以恒的努力可能在某些情况下造就天才,但我最终确信的还是,文学抱负不能仅仅解释为自由选择。我认为,这样的选择是必要的,但那是只有到第二个阶段才发生的事情,而从第一个阶段开始,即从少儿时期起,首先需要主观的安排和培养;后来的理性选择是来加强少儿期的教育,而不是从头到脚制造出一个作家。
如果我的怀疑没错的话(当然,很有可能不对),一个男孩或者女孩过早地在童年或者少年时期展示了一种倾向:能够想象出与生活不同的天地里的人物、情节、故事和世界,这种倾向就是后来可能称之为文学抱负的起点。当然,从这样一个喜欢展开想象的翅膀远离现实世界、远离真实世界的倾向,到开始文学生涯,这中间还有个大多数人不能跨越的深渊。能够跨越这个深渊、通过语言文字来创造世界的人们,即成为作家的人,总是少数,他们把萨特说的一种选择的意志运动补充到那种倾向里去了。时机一旦可能,他们就决定当作家。于是,就这样做了自我选择。他们为了把自己的抱负转移到书面话语上而安排了自己的生活,而从前这种抱负仅限于在无法触摸的内心深处虚构别样的生活和世界。这就是您现在体验到的时刻:困难而又激动的处境,因为您必须决定除去凭借想象虚构现实之外,是否还要把这样的虚构化作具体的文字。如果您已经决定这样做,那等于还要把这样的虚构化作具体的文字。如果您已经决定这样做,那等于您已经卖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当然,这丝毫不能保证您将来一定能当上作家。但是,只要您坚持下去,只要您按照这个计划安排自己的生活,那就是一种(唯一的)开始成为作家的方式。
这个会编造人物和故事的早熟才能,即作家抱负的起点,它的起源是什么呢?我想答案是:反抗精神。我坚信:凡是刻苦创作与现实生活不同的生活的人们,就用这种间接的方式表示对这一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表示用这样的拒绝和批评以及自己的想象和希望制造出来的世界替代现实世界的愿望。那些对现状和目前生活心满意足的人们,干嘛要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创作虚拟的现实这样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事情中去呢?然后,使用简单工具写作创作别样生活和别样人群的人们,有可能是在种种理由的推动下进行的。这些理由或者是利他主义的,或者是不高尚的,或者是卑劣吝啬的,或者是复杂的,或者是简单的。无论对生活现实提出何种质问,都是无关紧要的,依我之见,这样的质问是跳动在每个写匠心中的。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应该坚决、彻底和深入,永远保持这样的行动热情——如同堂吉诃德那样挺起长矛冲向风车,即用敏锐和短暂的虚构天地通过幻想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经过生活体验的具体和客观的世界。

但是,尽管这样的行动是幻想性质的,是通过主观、想象、非历史的方式进行的,可是最终会在现实世界,即有血有肉的人们的生活里,产生长期的精神效果。
关于现实生活的这种怀疑态度,即文学存在的秘密理由——也是文学抱负存在的理由,决定了文学能够给我们提供关于特定时代的唯一的证据。虚构小说描写的生活——尤其是成功之作——绝对不是编造、写作、阅读和欣赏这些作品的人们实实在在的生活,而是虚构的生活,是不得不人为创造的生活,因为在现实中他们不可能过这种虚构的生活,因此就心甘情愿地仅仅以这种间接和主观的方式来体验它,来体验那另类生活:梦想和虚构的生活。虚构是掩盖深刻真理的谎言,虚构是不曾有过的生活,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人们渴望享有、但不曾享有,因此不得不编造的生活。虚构不是历史的画像,确切的说,是历史的反面,或者说历史的背面;虚构是实际上没有发生的事情,因此,这样的事情才必须由想象和话语来创造,以便安抚实际生活难以满足的雄心,以便填补人们发现自己周围并用幻想充斥其间的空白。
当然,反抗精神是相对的。许多写匠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精神的存在,或许还有可能他们弄明白了自己想象才能的颠覆性质之后,会吃惊和害怕,因为他们在公公开场合绝对不认为自己是用炸弹破坏这个世界的秘密恐怖分子。另一方面说到底,这是一种相当和平的反抗,因为用虚构小说中那触摸不到的生活来反抗实在的生活,又能造成什么伤害呢?对于实在的生活,这些竞争又能意味着什么危险呢?粗略得看是没有的,这是一种游戏。不是吗?各种游戏只要补齐图越过自己的空间、不牵连到实在的生活,通常是没有危险的,好了,如果现在有人——比如,堂吉诃德或者包法利夫人——坚持要把虚构小说与生活混淆起来,非要生活得像想说你那个模样不可,其结果常常是悲惨的,凡是要这么行动的人,那往往要以可怕的失望作代价。
但是文学这个游戏也并非无害,由于虚构小说是内心对生活不满的结果,因此也就成为抱怨和宣泄不满的根源。因为,凡通过阅读体验到伟大小说中的生活,比如上面刚刚提到的塞万提斯和福楼拜的作品的人,回到现实生活时,面对生活的局限和种种毛病,其感觉会格外敏感,因为他通过作品中的美妙想象已经明白:现实世界——这实在的生活——比起小说家编造的生活不知要庸俗多少。优秀文学鼓励的这种对现实世界的焦虑,在特定的环境里也可能转化为面向政权、制度或者既定信仰的反抗精神。
因此在历史上,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是不信任虚构小说的,并实行严格的书刊审查,甚至在长达三百年的时间里禁止整个美洲殖民地出售小说。其借口是那些胡说八道的故事会分散印第安人对上帝的信仰,对于一个以神权统治的社会来说,这是惟一重要的心事。与宗教裁判所一样,任何企图控制公民生活的政府和政权,都对小说表示了同样的不信任,都对小说采取监视的态度,都使用了限制手段:书刊审查。前者和后者都没有搞错:透过那无害的表面,编造小说是一种享受自由和对那些企图取消小说的人一一无论教会还是政府的反抗方式。这正是一切独裁政权、法西斯、伊斯兰传统派政权、非洲和拉丁美洲军事专制政权企图以书刊审查方式强制文学穿上拘束服(限定在某种范围内)以控制文学。
可是,这样泛泛的思考让我们有些脱离了您的具体情况,我们还是回到具体问题上来吧。您在内心深处已经感觉到了这一文学倾向的存在,并且已经把献身文学置于高于一切的坚定不移的行动之中了。那现在呢?您把文学爱好当作前途的决定,有可能会变成奴役,不折不扣的奴隶制。为了用一种形象的方式说明这一点,我要告诉您,您的这一决定显然与十九世纪某些贵夫人的做法如出一辙:她们因为害怕腰身变粗,为了恢复美女一样的身材就吞吃一条绦虫。您曾经看到过什么人肠胃里养着这种寄生虫吗?我是看到过的。我敢肯定地对您说:这些夫人都是了不起的女杰,是为美丽而牺牲的烈士。六十年代初,在巴黎,我有一位好朋友,他名叫何塞·马利亚,一个西班牙青年,画家和电影工作者,他就患上了这种病。绦虫一旦钻进他身体的某个器官,就安家落户了:吸收他的营养,同他一道成长,用他的血肉壮大自己,很难、很难把这条绦虫驱逐出境,因为它已经牢牢地建立了殖民地。何塞·马利亚日渐消瘦,尽管他为了这个扎根于他肠胃的小虫子不得不整天吃喝不停(尤其要喝牛奶),因为不这样的话,它就烦得你无法忍受。可何塞吃喝下去的都不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快感和食欲,而是让那条绦虫高兴。有一天,我们正在蒙巴拿斯的一家小酒吧里聊天,他说出一席坦率的话让我吃了一惊:“咱们一道做了许多事情。看电影,看展览,逛书店,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谈论政治、图书、影片和共同朋友的情况。你以为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和你一样的吗?因为做这些事情会让你快活,那你可就错了。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了它,为这条绦虫。我现在的感觉就是:现在我生活中的一切,都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着我肠胃里的这个生物,我只不过是它的糊、甜蜜和忘却的梦想。这蠕虫在这之前就钻进我的心中,它蜷曲在那里,用我的大脑、精神和记忆做食粮。我知道,自己已经被心中的火焰抓住,已经被自己点燃的火吞食,已经被多年来耗费我生命的愤怒与无法满足的欲望铁爪撕得粉碎。一句话,我知道,脑海里或者心中或是记忆中,一个发光的细胞将永远闪耀,日日夜夜地闪耀,闪耀在我生命的每时每刻,无论是清醒还是在梦中。我知道那蠕虫会得到营养,永远光芒四射,我知道无论什么消遣,什么吃喝玩乐,都不能熄灭这个发光的细胞。我知道即使死亡用它那无限的黑暗夺去了我的生命,我也不能摆脱这条蠕虫。”我知道终于我还是变成了作家,我也终于知道了一个人如果要过作家的生活,他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想,只有那种献身文学如同献身宗教一样的人,当他准备把时间、精力、勤奋全部投入文学抱负中去,那时他才有条件真正地成为作家,才有可能写出领悟文学为何物的作品。而另外那个神秘的东西,我们称之为才能、天才的东西,不是以早熟和突发的方式诞生的,至少在小说家中不是,虽然有时在诗人或者音乐家中有这种情况,经典性的例子可以举出兰波和莫扎特,而是要通过漫长的程序、多年的训练和坚持不懈的努力才有可能使之出现。没有早熟的小说家。任何大作家、任何令人钦佩的小说家,一开始都是练笔的学徒,他们的才能是在恒心加信心的基础上逐渐孕育出来的。那些逐渐培养自己才能的作家的榜样力量,是非常鼓舞人的,对吗?他们的情况当然与兰波不同,后者在少年时期就已经是个天才诗人了。
假如对这个孕育文学天才的话题感兴趣,那么我建议您读读福楼拜的书信集,尤其是一八五0至一八五四年间他在创作第一部杰作《包法利夫人》时写给情人路易莎·科勒的那些信。我在写自己最初的那几部作品时,阅读这些书信让我受益匪浅。尽管福楼拜是悲观主义者,他的书信中充满了对人性的辱骂,但他对文学却有着无限的热爱。因为他把自己的抱负表现为参加远征,怀着狂热的信念日日夜夜投身其中,对自己苛求到难以形容的程度。结果,他终于冲破自身的局限性(在他早期的文字中,由于受流行的浪漫主义模式的影响而咬文嚼字、亦步亦趋,这十分明显)并且写出了像《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这样的长篇小说,可以说这是最早的两部现代小说。另一部与这封信的话题有关的作品,我冒昧地推荐给您,就是美国一位非常特别的作家威廉·巴勒斯写的《吸毒者》。巴勒斯作为小说家,我丝毫不感兴趣。他那些实验性、心理迷恋性的故事,总是让我特别厌烦,甚至让我觉得不能卒读。但是,他写的第一部作品《吸毒者》是有事实根据的,有自传性质,那里面讲述了他如何变成吸毒者、如何在吸毒成瘾后自由选择的结果,毫无疑问是某种爱好所致,变成了一个幸福的奴隶、快乐的瘾君子。我认为描写得准确无误,是他文学抱负发挥的结果,也写出了这一抱负在作家和作家任务之间的从属关系以及作家在写作中吸收营养的方式。
但是,我的朋友,对于书信体文字来说,我这封信已经超过了合适的长度,而书信体文字的主要优点恰恰应该是短小,因此我说声:再见吧。
拥抱您。

